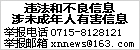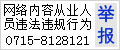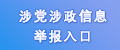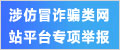“嗚嘟之父”畢寅生
我省“非遺”代表性傳承人專(zhuān)訪(fǎng)之二
夢(mèng)想,從竹笛起航
畢寅生1950年出生于武漢,從小就對(duì)音樂(lè)特別敏感。童年的時(shí)候,他常隨母親去戲園看戲,每每戲園笛聲響起,畢寅生都意馳神往。這樣的環(huán)境,給予畢寅生以極大的啟迪。
13歲的時(shí)候,畢寅生有了自己的第一件樂(lè)器——笛子。畢寅生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,他也非常珍惜這根笛子——應(yīng)該說(shuō)這是他的一個(gè)寶貴的學(xué)習(xí)音樂(lè)的機(jī)會(huì),雖然他并沒(méi)有真正地坐在音樂(lè)殿堂里學(xué)習(xí),甚至還沒(méi)有自己的音樂(lè)老師。
愛(ài)好,毅力,就是畢寅生最好的啟蒙老師。每天早上,他都會(huì)雷打不動(dòng)地跑到武漢中山公園或長(zhǎng)江邊上吹笛,練長(zhǎng)音、練氣息。優(yōu)美的樂(lè)曲,沖淡了畢寅生童年生活的艱苦,吹散了他心中的煩惱和憂(yōu)愁,還讓他交上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笛友。
畢寅生的笛子越吹越好,在學(xué)校里,只要有什么文藝演出,都缺不了他的表演。在老師的推薦下,畢寅生參加了學(xué)校宣傳隊(duì),進(jìn)步神速。
漸漸地,畢寅生不滿(mǎn)于現(xiàn)狀了,他想繼續(xù)深造,想進(jìn)入音樂(lè)的殿堂。機(jī)緣巧合,他前后拜武漢歌舞劇院著名笛子演奏家孔建華為師。通過(guò)孔老師,他又認(rèn)識(shí)了很多音樂(lè)界的大師,其中最讓他難忘的就是中國(guó)古塤演奏第一人——趙良山老師。最為人感動(dòng)的是,趙良山原來(lái)在省歌舞團(tuán)里吹塤,后來(lái)他要調(diào)到廈門(mén)大學(xué)任教,樂(lè)隊(duì)里缺少一位吹塤人,趙老師就向樂(lè)團(tuán)鄭重推薦了畢寅生。臨行前一個(gè)星期,趙老師更是把塤的吹奏技藝和心得傾囊相授。
因種種原因,畢寅生最終與樂(lè)團(tuán)失之交臂,但是能得到趙良山老師的悉心栽培,他亦覺(jué)得沒(méi)有什么遺憾了。
嗚嘟,冥冥中的牽絆
中國(guó)的土類(lèi)樂(lè)器有二,塤和嗚嘟。有時(shí)候命運(yùn)就是這么奇特,在師從中國(guó)古塤演奏第一人趙良山多年以后,畢寅生竟和老師的命運(yùn)奇跡般地重合了——他擔(dān)起了另一種土類(lèi)樂(lè)器——嗚嘟的改良和推廣使用的歷史使命。
1970年,畢寅生招工進(jìn)了原嘉魚(yú)棉紡廠(chǎng);1985年,因?yàn)槲乃囂亻L(zhǎng),他被調(diào)到了嘉魚(yú)縣文化館。1986年,文化部下發(fā)通知,將舉辦全國(guó)性的“三民”(民歌、民舞、民樂(lè))比賽,當(dāng)時(shí)咸寧地區(qū)群藝館的游伯樵老師經(jīng)過(guò)民間走訪(fǎng)和調(diào)查后決定,把嘉魚(yú)民間用泥巴捏成的泥哨子進(jìn)行技術(shù)改進(jìn),做成吹奏樂(lè)器去參賽。考慮到畢寅生精湛的吹奏技巧,這個(gè)任務(wù)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身上。
畢寅生根據(jù)自己在省歌舞劇院里學(xué)過(guò)的樂(lè)器和樂(lè)理知識(shí),把泥哨子的哄鳴腔體擴(kuò)大,增加了音孔,改變吹口的斜度,使泥哨子發(fā)生了質(zhì)的變化,成了音樂(lè)優(yōu)美、穿透力強(qiáng)、音準(zhǔn)高、音域達(dá)11度的土類(lèi)吹奏樂(lè)器,這就是嗚嘟。畢寅生還根據(jù)嗚嘟的特點(diǎn),他創(chuàng)作了樂(lè)曲《野洲情趣》。在這年的“三民”賽上,畢寅生不負(fù)眾望,一曲《野洲情趣》吹奏下來(lái),獲得了創(chuàng)作和演奏兩項(xiàng)銅獎(jiǎng)。
“三民”賽讓嗚嘟一舉成名,也促成了畢寅生人生的轉(zhuǎn)折。在這之后,畢寅生經(jīng)常應(yīng)邀參加各種演出,吹奏嗚嘟。1995年,央視《東方之子》為他錄制了8分鐘的專(zhuān)題節(jié)目;2000年,畢寅生隨中國(guó)殘疾人藝術(shù)團(tuán)出訪(fǎng)美國(guó),先后在華盛頓、紐約等5個(gè)城市表演嗚嘟獨(dú)奏。在夏威夷,畢寅生由中國(guó)殘聯(lián)主席鄧樸方陪同,還特意到張學(xué)良的家中為他吹奏了嗚嘟等樂(lè)器。
在卡內(nèi)基音樂(lè)廳演出,畢寅生記憶猶深。“卡內(nèi)基音樂(lè)廳是美國(guó)古典音樂(lè)與流行音樂(lè)界的標(biāo)志性建筑,其主廳的休息室裝飾有在這里演出過(guò)的名人和團(tuán)體的簽名畫(huà)像和紀(jì)念畫(huà)。在那里,我發(fā)現(xiàn)我們是第一個(gè)進(jìn)卡內(nèi)基音樂(lè)廳表演的華人團(tuán)體,心里很激動(dòng)。這是美國(guó)人對(duì)我們藝術(shù)的承認(rèn)和尊重。”而外國(guó)演奏家對(duì)藝術(shù)的虔誠(chéng)和嚴(yán)謹(jǐn)態(tài)度,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,也讓他感動(dòng)不已。
愛(ài)恨,嘔心瀝血不悔
藝術(shù)道路是一條鋪滿(mǎn)鮮花的陽(yáng)光之旅,同時(shí)也是一條艱難漫長(zhǎng)的“不歸”之路。把樂(lè)器演奏作為職業(yè),半生輕松;把嗚嘟的推廣和改良當(dāng)作事業(yè),注定一世辛苦。
從1986年與嗚嘟打交道以來(lái),已過(guò)去23個(gè)春秋。畢寅生為嗚嘟反復(fù)探索,拓展其音域、音準(zhǔn)音樂(lè),發(fā)表各類(lèi)論文和研究報(bào)告,進(jìn)行音學(xué)測(cè)試,并獲得了國(guó)家專(zhuān)利。
畢寅生說(shuō),“很多人以為我借嗚嘟出了名、出了國(guó)。實(shí)際上,從1986年參加‘三民’賽把嗚嘟推出去了之后,我一直沒(méi)有停下研究的步伐,一直在發(fā)展和完善它。”不過(guò),在出外演奏和講授時(shí),還是有不少人把嗚嘟和塤混為一談。更有人說(shuō),“嗚嘟不過(guò)是在古老的泥哨子上多加了幾個(gè)孔而已……”這些,讓畢寅生寒心不已。他說(shuō),“嗚嘟與塤比起來(lái),音樂(lè)更為渾厚,穿透力更強(qiáng)。因?yàn)閺目谏谘葑兌鴣?lái),所以易發(fā)音,易學(xué)。作為影視的配樂(lè),表現(xiàn)幽怨、縹渺、悲壯的格調(diào)獨(dú)一無(wú)二。”
愛(ài)之深,才會(huì)恨之切。畢寅生在博客里不止一次罵道:“嗚嘟這個(gè)鬼東西”。他解釋說(shuō):“說(shuō)愛(ài)嗚嘟,是因?yàn)樗且环N責(zé)任,只要我們中國(guó)有這樣一個(gè)土類(lèi)樂(lè)器,并且通過(guò)了這么長(zhǎng)時(shí)間的發(fā)展,就應(yīng)該在中國(guó)的音樂(lè)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說(shuō)恨,是因?yàn)檫@么多年來(lái),我去愛(ài)護(hù)它,保護(hù)它,維護(hù)它,犧牲了很多。為了不放棄一次展示嗚嘟的機(jī)會(huì),母親病重中,我原本是想早些回家的,卻因嗚嘟耽擱了。等我回到家時(shí),母親已經(jīng)走了……我想念母親,心里一直很愧疚。這么多年來(lái),嗚嘟的前景還是不樂(lè)觀。雖然有廠(chǎng)家生產(chǎn)嗚嘟了,但很多人還是把它當(dāng)藝術(shù)品把玩鑒藏,而不是把它當(dāng)樂(lè)器看待;而嗚嘟在樂(lè)器的生產(chǎn)工藝上,還有很大的進(jìn)步空間。”
累也累了,苦也苦了,愛(ài)也愛(ài)了,恨也恨了,畢寅生并不后悔為嗚嘟的付出。他說(shuō),作為一名基層的文化工作者和科研者,我做了自己應(yīng)該做的事。“納西古樂(lè)為什么能夠一代代傳承下來(lái),因?yàn)樗麄兊膫魅硕加幸魳?lè)感,會(huì)識(shí)譜、會(huì)演奏,他們能把音樂(lè)發(fā)揚(yáng)光大。作為一名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的傳承人,應(yīng)該利用自己的樂(lè)器知識(shí)繼續(xù)完善嗚嘟,用自己的樂(lè)理知識(shí)創(chuàng)作出更多適宜于演奏的曲調(diào)來(lái)。”
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的快節(jié)奏生活,快餐文化當(dāng)?shù)溃诵牟还牛莒o心坐下來(lái)欣賞嗚嘟的人很少,有志于學(xué)吹奏嗚嘟的人更少。想起嗚嘟的勢(shì)微,畢寅生又很心焦。為此,他在嘉魚(yú)縣城成立一間音樂(lè)教室,與女兒一起教授嗚嘟、古箏、鋼琴等樂(lè)器演奏,除此以外,他還在音樂(lè)教室里開(kāi)設(shè)了國(guó)畫(huà)班。“嗚嘟教學(xué)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,搞音樂(lè)教室如果只教嗚嘟,難以立足。現(xiàn)在我又教國(guó)畫(huà)又教音樂(lè),也是曲線(xiàn)救嗚嘟吧!”
臨別時(shí),畢寅生拿出嗚嘟為我們吹奏了一曲。嗚嘟聲聲,音色古樸醇厚、圓潤(rùn)清麗,讓人如墜云間。清幽時(shí),國(guó)畫(huà)課室墻上貼著的國(guó)畫(huà)啞然失音;高亢時(shí),那些墻上的畫(huà)像是被陶醉了,在墻上頻頻點(diǎn)頭晃腦,屋子里的桌椅、畫(huà)架像被音樂(lè)附體,恍惚像魚(yú)兒一樣在空氣中翔游……一曲撲面而來(lái)的豪歌柔韻,一份被吹奏者慨然相贈(zèng)的美意與輕松,讓我們感受到了嗚嘟這古老的樂(lè)器對(duì)我們靈魂安慰的絮語(yǔ)與愛(ài)撫的溫暖。
但愿這種樂(lè)器能代代相傳,能溫暖和愛(ài)撫更多的心靈……
(記者 葉和平 杜培清) (載《南鄂晚報(bào)》3月17日《副刊》)
作者:liuhuafang
編輯:Administrator
相關(guān)新聞
-
穿越時(shí)空的樂(lè)器——盆鼓

擊鼓而戰(zhàn)、擊鼓而歌、擊鼓而舞,這是鄂南文化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的一枝奇葩——盆鼓。雖飽經(jīng)滄桑,卻歷久彌新。 “盆鼓”,又稱(chēng)“...
-
撥動(dòng)歷史的脈搏——拍打舞

“干完活,歇歇火,拍拍打打呀咿子喲。我拍你,你拍我,拍走辛苦就快活。拍拍打打真高興,叫聲伙計(jì)漲點(diǎn)勁。漲勁拍得事事順,...
-
從戰(zhàn)場(chǎng)走向田間——山鼓

三千年的歷史,恍如一瞬。那吳楚交兵的聲聲戰(zhàn)鼓,依然回響在人們的心頭。走近首批省級(jí)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——山鼓,我們可以聆聽(tīng)...
-
稀有的藝術(shù)奇葩——提琴戲

一個(gè)稀有文化物種,在光怪陸離的現(xiàn)代藝林,奇特地芬芳著,這就是咸寧崇陽(yáng)提琴戲! 在我國(guó)300多個(gè)戲曲劇種中,提琴戲,...
-
黃土捏出的天賴(lài)——嗚嘟

約2000年前,一個(gè)咸寧嘉魚(yú)的牧童,用腳下的泥土,捏成世界上第一個(gè)泥哨子,這就是被稱(chēng)之為“天籟之音”嗚嘟的前身。 說(shuō)...
-
崇陽(yáng)提琴戲的繁榮之道
-
提琴戲三盼
-
河南兩豫劇劇目入選全國(guó)地方戲精粹展演
12月6日,記者從省文化廳獲悉,由國(guó)家文化部主辦的全國(guó)地方戲精粹展演活動(dòng)將于12月19日在北京開(kāi)幕。省豫劇二團(tuán)的豫劇《程嬰救...
-
《雷雨》參加全國(guó)地方戲展演
近日,上海滬劇院傳出消息,經(jīng)典滬劇《雷雨》將代表上海戲曲院團(tuán),于明年1月8日、9日與全國(guó)各地區(qū)18臺(tái)劇目一起參加由國(guó)家文化...
-
隴劇《楓洛池》拉開(kāi)全國(guó)地方戲精粹展帷幕
早在1959年,作為隴劇開(kāi)山之作的《楓洛池》進(jìn)京向國(guó)慶10周年獻(xiàn)禮演出,一經(jīng)亮相火爆異常,連演20多場(chǎng),并兩次走進(jìn)中南海懷仁...
① 凡本網(wǎng)注明"來(lái)源:咸寧網(wǎng)"的所有作品,版權(quán)均屬于咸寧網(wǎng),未經(jīng)本網(wǎng)授權(quán)不得轉(zhuǎn)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(jīng)本網(wǎng)授權(quán)使用作品的,應(yīng)在授權(quán)范圍內(nèi)使用,并注明"來(lái)源:咸寧網(wǎng)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(wǎng)將追究其相關(guān)法律責(zé)任。
② 凡本網(wǎng)注明"來(lái)源:xxx(非咸寧網(wǎng))"的作品,均轉(zhuǎn)載自其它媒體,轉(zhuǎn)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(wǎng)贊同其觀點(diǎn)和對(duì)其真實(shí)性負(fù)責(zé)。
③ 如因作品內(nèi)容、版權(quán)和其它問(wèn)題需要同本網(wǎng)聯(lián)系的,請(qǐng)?jiān)?0日內(nèi)進(jìn)行。

編輯推薦
- 1咸寧開(kāi)設(shè)304個(gè)“愛(ài)心托管班” 托起1.2萬(wàn)名少年
- 2尋訪(fǎng)抗戰(zhàn)印跡 傳承復(fù)興力量 全國(guó)地市媒體紀(jì)念抗
- 3咸寧職工互助保障撐起健康“保護(hù)傘” 最大單筆
- 4全國(guó)智慧法院創(chuàng)新案例揭曉 咸寧市一個(gè)案例上榜
- 5全省“三大精神”主題紅色資源推介名錄發(fā)布?咸
- 6通武高速湖北段通車(chē)
- 7咸寧市中小學(xué)暑假時(shí)間確定?7月6日至8月31日
- 8致全體市民的感謝信 —— 寫(xiě)在咸寧榮獲全國(guó)文明
- 9全國(guó)少先隊(duì)表彰名單公布 咸寧市1人1集體上榜
- 10咸寧市新增兩個(gè)省級(jí)全域公交縣
娛樂(lè)新聞
-
人藝“經(jīng)典保留劇目恢復(fù)計(jì)劃”開(kāi)篇之作 《風(fēng)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(mǎn)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