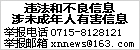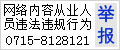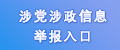帶我去飛翔
■ 作者: 吳亮
太陽徐徐下山了,一片金黃色的光輝籠罩著營房對面那座挺拔秀麗的山,仿佛整個天空被涂上了一層金黃色的水彩,美得炫目。
呂政委就是在這樣柔和的夕陽下悠閑地走在林間小路上。
突然,一個女孩急步朝小路上走來,走到呂政委的面前“叭”地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,望著呂政委怯生生地說,政委,您好!我懇求您幫我一個忙好嗎?
呂政委微笑著親切地問,夏菁同志,你有什么事?
女孩輕輕地說,我想去西藏!
呂政委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,什么?你要去西藏?
夏菁說了原因,其實說了等于沒說,因為她說的是,是的,我覺得西藏好。
再問,就什么也不說了。
一片彩云飄過頭頂的天空。朦朦朧朧的天色下,一滴晶瑩的淚珠在夏菁的眼眶里打轉,她感到鼻子又一陣發酸,她輕輕眨了眨眼睛,沒讓眼淚流下來。
山那邊,夕陽慢慢地躲進了地平線。
十幾天之后的又一個傍晚。
柔和的夕陽下,女孩的身影又一次撞入了呂政委的視線中,她坐在河邊的石頭上,輕輕地托著腮,一動不動地望著遠方。望著這個女孩,呂政委突然涌起一股想跟她聊一聊的欲望。
正在怔怔發呆的夏菁完全沒有覺察呂政委已坐在她的旁邊,當呂政委叫她時,她轉過頭來,慌亂地用手背擦了擦眼睛,并朝呂政委笑了笑,盡管這樣,呂政委還是從她濕潤的瞳孔里看出她剛剛哭過。他親切地問她發生什么事了。夏菁沒有回答,重復了上一次的請求。
呂政委說,孩子,放棄這個想法吧,西藏的生活實在太艱苦了。
夏菁聽了靜靜地說,我知道!她的神情中有一種叫平靜的東西,在她仍殘留著一絲稚氣的臉上,呂政委看不到年輕人所慣有的那種浮躁。她仿佛一汪平靜的湖水,靜靜地任人閱讀。
又仿佛一塊石頭投進湖中,打破了湖面的平靜。西藏的話題就像一塊巨大的石頭,擊進了夏菁看似平靜的心湖里。她娓娓而談,談西藏的雪,談西藏的風,談西藏的哨所,談西藏的官兵……她的訴說是帶有感情的,就像親身經歷的人才有的真切體會。
呂政委不解,是書上看的嗎?
不,一個人!一個真正的軍人!
女孩的目光變得遙遠而深情……
她和他是總隊招收的同一批大學生,他們是在天津指揮學院培訓時認識的。他們第一次面對面地正視對方,是在去實習部隊的車上。那天,當夏菁上到接他們的車上時,除了接送的干部和開車的司機,只有她和另外一個男兵。他叫鄒哲軍,一張棱角分明的臉似乎剛剛刻上剛毅的線條,在閃著光輝的軍帽的映襯下,展示出一種力度的張揚,草綠的軍裝穿在他挺拔的身上,使他渾身上下散發出一種軍人特有的氣質。在汽車奔馳的一路上,他們慢慢的聊了起來……
到了實習的部隊后,他們自然就成了好朋友。空閑之時,他們經常在一起聊天。日子在快樂和滿足中這樣悄悄過去。突然有一天,情竇初開的夏菁,發現自己的日記中越來越多了鄒哲軍的名字,詩行中也不停閃現著鄒哲軍的影子,她悄悄地保守著這份秘密,一個人獨享這個秘密的神秘和甜蜜。在此后時間流過的歲月里,夏菁的心一直被一種溫情深深地包圍著。
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日,夏菁和鄒哲軍相約去爬山。南國的木棉花像一個個用紅墨水染成的肥碩的感嘆號,映紅了山的笑臉,也映紅了他們年輕的笑臉。天在不知不覺中下起了大雨,他們躲在同一把傘下,鄒哲軍撐的傘。他們不約而同的在傘下沉默不語,突然鄒哲軍輕輕地說,夏菁,你愿意讓我永遠為你撐傘嗎?……
未來在他們的眼前展開了一幅美好燦爛的圖畫。他們一起憧憬著未來,一起期待著明天。他們商議好了,畢業一起向組織申請分回南方夏菁的家鄉,那是他們夢的開始的地方,更是他們緣分的發源地。他們留戀那片一年四季都充溢著綠色的土地,就像深深愛戀他們之間純美的情誼。
分配結果宣布了,夏菁被分到了南方城市的一個支隊擔任宣傳干事,可鄒哲軍被分到了西藏。
很快的,呼嘯的列車無情地拉開了人們的距離,牽動著追隨的目光,也扯痛了思念的心弦。站臺上的別離是一出出凄美的故事,夏菁和鄒哲軍只是某一出故事里的一段而己。鄒哲軍似一只蒼勁的雄鷹,撲向了遠方那片茫茫的雪域高原。夏菁在另一座南方小城里,像一只棲候的小鳥,永遠作著等待的姿勢,目光被拉扯得很長很長……
鄒哲軍時常寫信回來向夏菁描繪高原的高潔與粗獷,也訴說塵沙的殘暴與張狂,當然還有許許多多有趣卻讓人聽起來心酸的事。
鄒哲軍喜歡南方。南方,遙遠而美麗!但是,他更愛高原。愛高原的戰士,愛高原的每一份生命的美麗,愛高原生命里的每一份堅強。
一只鷹常常在駐地赤紅的上空盤旋,作出短促而悠遠的歌唱,嘹唳地,清脆地。
鷹是我所愛的。它有著兩個強健的翅膀。鄒哲軍在信中說。
鷹的歌聲是嘹唳而清脆的,如同一聲聲嘹亮的軍號。而當這軍號聲響起來的時候,我就忘卻艱苦和寂寞而感覺興奮了。鄒哲軍在信上說。
每一個守望的日子,一只鷹飛過的痕跡深深鉻在夏菁的心上。她決定申請進藏,像鄒哲軍一樣,展開飛翔的翅膀,去追尋生命的高潔和青春的燦爛。她的決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對,也遭到了鄒哲軍的強烈反對……
夏菁,不要。請不要來西藏,你是南國一片嬌嫩的葉子,你的顏色會染綠南方的天空,但它經不起高原太陽的暴曬和風沙的襲擊,我不忍心讓它受高原風雪的摧殘。
請原諒!其實,分到西藏是我自己申請的,宣布之前沒有告訴你,是怕你知道后要跟我來,雖然我非常希望我們能一起來,但我知道我不能……
我來西藏,不僅僅是因為這里更能充分發揮我人生的光和熱,更因為這里有我父親的足跡,有我父親的靈魂……
最后一個寒假快要結束了。在返校的前一天晚上,鄒哲軍陪在母親的身邊,就像每一次離家一樣,壓抑不住內心的酸楚。突然,母親起身回屋捧出一個木匣子,神情嚴肅地打開它,內有一套疊得整整齊齊的泛白的老軍裝,上面有幾處凝固了的血跡,還有一個閃著光輝的軍功章,除此之外,還有一張發黃的黑白照片。母親指著照片上的那個男人對鄒哲軍說:“孩子,這就是你的父親。”從小,鄒哲軍就沒有父親,母親告訴他,父親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;再大些,母親也是這樣說,懂事的鄒哲軍知道母親不愿意說,也就不再問了。母親語重心長地告訴鄒哲軍,她之所以今天才讓他知道父親的死,是因為鄒哲軍已真正成了一名軍人,也能正確理解父親犧牲的意義了。母親說,父親的軍人生涯在西藏,父親的愛在西藏,父親的靈魂也在西藏,父親把短暫絢爛的生命也獻給了西藏。
那晚,鄒哲軍摸著父親的軍裝和軍功章,失眠了,第二天早晨用充滿了血絲的眼睛定定地看著母親說我要去西藏,母親沒同意也沒有反對,望著高出自己整整一個頭的兒子那年輕而剛毅的臉,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,說,你已是一個大人,也是一個軍人了,你認為該做的事就去做吧。鄒哲軍知道,父親不僅僅點亮了自己的生命,也鑄就了母親的堅強與豁達。
既然鄒哲軍不同意你進藏,現在你為什么又執意要去呢?趁著夏菁停下歇氣的空隙,呂政委忍不住問。
夏菁艱難地笑了笑,其實沒有他們的反對,我那一次一樣去不成西藏,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西藏。
那么你現在有足夠的勇氣了嗎?是愛情的力量吧!
不!他已經死了……夏菁已泣不成聲。
鄒哲軍是在一次去哨所巡邏的路上和司機一起連人帶車翻下山巖的。部隊找不到他們的尸體,他年輕的生命和高原的白雪已融為一體,那是高原熾熱而燦爛的太陽。他靜靜地躺在雪堆寬闊的臂彎里,照耀著白雪的冰凍與寂寞。
不遠處,一只鷹在天空之中飛翔著,伸展著兩個翅膀,傾側著,回旋著,作出了短促而悠長的歌聲。
在呂政委的極力幫助下,夏菁很快的去了西藏,她這一極不尋常的調動,在部隊內部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,他們紛紛猜測夏菁此事的目的,說法很多,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,她是為了去完成她深愛的男孩未了的事業,除了呂政委。
隨著夏菁的離去,人們慢慢的忘記了她的不尋常之舉,也漸漸忘記了她,只有呂政委在繁忙的工作之后,仍在報刊雜志上尋找她的名字。直到有一天,他在一本雜志上看到她的這樣一段文字:
激烈的情感動蕩之后心靈復歸于平靜,如潮汐漸漸退去,帶走了風中飄舞的塵沙,又留下了一絲絲痕跡。在粗獷與豪放中,你是一只纖纖小鳥,粗獷的高原風把你托起,你的肩膀依然稚嫩,陶醉于藍天的接近、白云的繚繞和草原的心曠神怡,卻再也無法不依戀那片神奇的土地,你堅如磐石地追尋著那些光輝的足跡,藍天白云裊裊,升騰起你青春的光芒……
呂政委微微地笑了。
窗外,一只鷹劃過赤紅的天空,留下一條優美的弧線!
(作者聯系地址:通城縣馬港鎮)
作者:yourui0503
編輯:Administrator
相關新聞
-
古代小說中的談文論藝
作者常攀附經史等強勢文體以自高,并在小說中談文論藝,以示博學,提高小說的品位,因此,小說中蘊藏著豐沛的文論資源,值得...
-
通山小說《玉竹譜》舉行首發式
咸寧網訊特約記者徐大發報道:近日,通山縣女作家倪霞的長篇小說《玉竹譜》在當地舉行首發式。小說探尋家族延續的內在精神脈搏...
-
將小說敘事置于歷史邏輯之中——讀網絡文學作品《燕云臺》

在表現秦宣太后歷史的《羋月傳》之后,又創作了長篇歷史言情小說《燕云臺》。從“言情文”的脈絡上來看, 《燕云臺》一洗《甄...
-
陪父母進餐館

通城有個吃手抓羊排的地方,裝修別致,環境優雅,餐品豐富,味道不錯。還有個特別之處是,每天晚上七點以后,便有幾個音樂愛...
-
過年那些事

故鄉是江南水鄉的一條小街,叫老新街。街前有一條河,叫金水河。那時候,街上各種商鋪應有盡有。每天天剛亮,從西涼湖、渡普...
-
熱騰騰的親情

年初三,給大伯拜年的時候,年逾古稀的大伯嗔怪我為什么不把孩子一起帶來。 我忙著解釋:“成天帶著孩子被他們鬧夠了,好...
-
小城春節

又是一年新春時,不論城市或者鄉村全沉浸在濃濃的節日氣氛中。忽然意識到這么多年,我的大部分春節都是鄉村度過的。成家后,...
-
父親的扁擔

父親的扁擔光滑,灰舊,著肩的地方赭紅。日出,它在父親的肩上,日落,它在門后旮旯里。父親用這扁擔挑出了人生一輩子幸福,...
-
圈子外的人

老江這段時間非常的郁悶,經常茶飯不思、坐臥不寧。老婆小陳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這不,乘著夜色怡人,強行拽著他到中央公...
-
我的奶奶

一直以來,想寫一篇關于我奶奶的文章,尤其在她去年7月患乳腺癌之后,這件事一直壓在我心里,今天終于下了決心,在這個寂靜的...
① 凡本網注明"來源:咸寧網"的所有作品,版權均屬于咸寧網,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并注明"來源:咸寧網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。
② 凡本網注明"來源:xxx(非咸寧網)"的作品,均轉載自其它媒體,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
③ 如因作品內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30日內進行。

娛樂新聞
-
人藝“經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”開篇之作 《風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