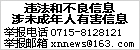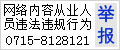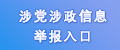桐花情
桐花凋落的日子,病痛襲來,我住進了醫院。
這春夜,風中帶著暖意,盡管我看不到紅的花、綠的葉,卻分明感知,春天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走進了病房。這樣的夜,適合想念……
我是在桐樹花開的季節認識她的。二十年前,工作后的第二個月,她以土地工子女的身份進企業(企業為了征用當地村民的土地,為村民或其子女安排工作)。黑瘦、矮個子,像男人一樣的短發,粗聲大氣說話,與我們這些經過多次量身高、稱體重、筆試、層層篩選進來的外地人成了鮮明的對比。更要命的是,她有個俗不可耐的名字:六元。為此,同事們在斜著眼看她時,常常戲謔她:幾元啊,你就值六元?她卻漲紅了臉,急急地爭辯:我爸取的,不怪我。家人都叫我元寶。頓時,人群又爆發一陣哄笑。
那時崗前要培訓,做筆記,背工作法,難倒了只上過小學的她,我主動提示她記憶和考試重點,幫她一次次通過考核。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,兩人越走越親近。
春天,她會帶著我到近郊抽竹筍、摘山泡、扯苦菜,將映山紅用藤條編成花環戴在彼此頭上,一起在山頂勾肩搭背,唱跑調的流行歌。
偶爾,她會在上班時偷偷繞到我身后,用膝蓋拱我的腘窩,當我猝不及防快倒地時笑呵呵地扶住我,變戲法似的拿著存折在我面前炫耀:又存了多少錢。不用驚詫,下班后,她回家種菜插秧割谷打麥子,賣農作物的收入比上班高得多。
我那時在基層搞管理,常有地頭蛇和我對著干,她一得訊就一陣風似的跑到我跟前,捋起袖子朝對方吼:“想欺負人啊?有本事就沖我來!”那架勢簡直就是誰敢動我,她就和誰拼命。看著矮我半頭的她,我找到了友情最準確的注解。
婚后的她生了女兒尚不滿足,又懷上后來的兒子。那時計生抓得緊,她用白紗布纏住日益隆起的腹部,穿寬大衣服,八個多月了還堅持上班,產量還是班上的前幾名,誰也看不出她是孕婦。生完兒子第四天她就面浮腳腫地來上班。我在心痛之余,慶幸蒼天有眼,祈愿兒女雙全的她,能過上好日子。
一天,她來找我,說在家鄉買了塊地,要辭工建房子。我急了:你不是有了新房嗎?要知道,許多像她一樣的雙職工還窩在一間平房里。“你還不知道我?別人沒有的,我想有;別人有的,我想更好!”
一個月后的那個雨天,我在辦公室窗前,看窗外粉的桃花、白的梨花紛紛揚揚,大朵大朵的桐花落滿一地,有些傷感。同事匆匆跑來:阿麗,你快去,六元喝藥了。
在醫院的搶救室里,她疲憊的眼睛再也沒睜開,我的心痛得揪在一起。她一個人和水泥、挑磚、提灰桶砌墻,四十多天才造起一層樓;而她那不成器的丈夫,卻日日在麻將館流連。不管她多么要強,在一次次堅持、無助、彷徨、失望中,找不到解脫、變通的途徑,最終徹底崩潰走向絕路,是何等的無奈與悲涼。
七年了,她早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去。而這些年,從她早逝的傷痛中,我感悟生命存在的意義,不為追求財富而忽視內心的成長。就算打擊再大磨難再多,就算三九寒冬,有朋友的關愛和支持,我也能感覺日日如沐春光。
就像此刻病中的我,床頭,有怒放的康乃馨;枕邊,有可以充實心靈的書籍;室外,有關不住的滿園春色。回憶著往昔的友誼,讓我思念與感動,感恩生命是這樣的豐富可貴。 (網友 窗外的流螢)
編輯:Administrator
① 凡本網注明"來源:咸寧網"的所有作品,版權均屬于咸寧網,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并注明"來源:咸寧網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。
② 凡本網注明"來源:xxx(非咸寧網)"的作品,均轉載自其它媒體,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
③ 如因作品內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30日內進行。

娛樂新聞
-
人藝“經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”開篇之作 《風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