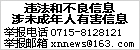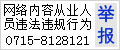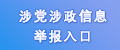愧對父親
一年一度,草木枯榮,轉(zhuǎn)眼又到清明。這個時候,家鄉(xiāng)的山野,開滿了杜鵑,葳蕤燦爛。鄉(xiāng)人們開始絡(luò)繹不絕地踏青祭祖,緬懷親人。清晨,站在窗前,朝著故鄉(xiāng)的方向凝望,不由想起年過半百的父親。
父親7歲時,家里經(jīng)常吃了上頓沒下頓。一次,饑腸轆轆的父親在山地里偷一個山芋,讓人追趕了整整一個村莊。秋收后,父親總是蹲在田間地頭,撿拾一根根稻穗,交給奶奶。那個年代,父親為了溫飽吃了不少苦。這些都是他臥病在床時與我談起的。
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過。父親一直在外打工,只有過年才回家?guī)滋臁K』丶抑委熌悄辏艺x初一。我們天天相見,漸漸地,他開始與我聊天。這時,我才知道他真實年齡,知道他會拉二胡,吹笛子。他給我講,奶奶死得早,他在我這個年紀(jì)已經(jīng)跟爺爺學(xué)手藝,曾經(jīng)餓著肚子挑200多斤的稻子走了50里路等等。
他感覺自己時日不多了,于是更加嘮叨,將他大半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地“抖摟”出來,恨不得把他這輩子的經(jīng)驗都一股腦兒地全塞給我。而那時的我,正值青春年少,根本無法理解他的苦楚,對他的嘮叨也只感到無奈煩悶。
曾與他大吵一場,在一個春日的下午。他坐在搖椅上,我靠著門欄。我大聲朝他吼,怪他無能,在外那么多年,家還是土瓦房子。除了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,家里什么電器也沒有。每次開學(xué)交學(xué)費,我和姐姐交的都是白條。老師天天催我們要學(xué)費,我在同學(xué)面前抬不起頭。
父親被病魔折騰得骨瘦如柴,神情枯槁。我對他叫嚷時,他的嘴唇被氣得發(fā)紫,哆哆嗦嗦地把身旁的茶杯推到了地上。“哐當(dāng)”一聲,玻璃碎片濺了一地。他大喊“不孝子”,使了全身力氣。隨后就一直喃喃自語著,說自己太苦,養(yǎng)了這么個不孝的兒子。我靠坐在門檻上,沉默了。我多么希望他還能像5年前,一手拎起我,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,那樣地剛勁有力。可現(xiàn)在,他的手青筋暴突、顫抖無力。我開始懊悔……我抱頭肆無忌憚地痛哭,哭坐在搖椅上病怏怏的他,哭我多年殘缺的父愛。
那是我與父親惟一一次的爭吵,也是我對他最清晰的記憶。就在次年的春天,他病情加重,臥床不起。我永遠(yuǎn)不會忘記,又一個春日的夜晚,他匆忙地走了,在我趕回家之前。母親告訴我,他走的時候眼睛沒合上,他沒看到我回來。我急促的腳步還是沒能追趕上他最后的牽掛。我跪在他的靈前痛哭,我恨自己的少不更事,恨作為兒子的無知不孝,恨沒能對他說一聲“對不起”……
時光易老,歲月無情。如今,他靜靜地躺在山腰,我的心仍充滿惆悵。爸,今年清明如果您的墳前盛開了一叢杜鵑花,那便是我跨越了千山萬水的愧疚與懷念。(汪亭)
編輯:Administrator
① 凡本網(wǎng)注明"來源:咸寧網(wǎng)"的所有作品,版權(quán)均屬于咸寧網(wǎng),未經(jīng)本網(wǎng)授權(quán)不得轉(zhuǎn)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(jīng)本網(wǎng)授權(quán)使用作品的,應(yīng)在授權(quán)范圍內(nèi)使用,并注明"來源:咸寧網(wǎng)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(wǎng)將追究其相關(guān)法律責(zé)任。
② 凡本網(wǎng)注明"來源:xxx(非咸寧網(wǎng))"的作品,均轉(zhuǎn)載自其它媒體,轉(zhuǎn)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(wǎng)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(fù)責(zé)。
③ 如因作品內(nèi)容、版權(quán)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(wǎng)聯(lián)系的,請在30日內(nèi)進行。

編輯推薦
- 12025年第三次“中國好人榜”候選人事跡展示評議
- 2咸寧高新區(qū)2家企業(yè)摘得湖北省科學(xué)技術(shù)獎
- 3第八屆“南鄂杯”高層次人才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業(yè)大賽初賽啟
- 4咸寧市新增10件國家地理標(biāo)志保護產(chǎn)品
- 5咸寧首個“擁軍驛站”揭牌?打造全域尊崇軍人服
- 6第三屆“楚茶杯”斗茶大賽結(jié)果揭曉?咸寧斬獲13
- 7咸寧開設(shè)304個“愛心托管班” 托起1.2萬名少年
- 8尋訪抗戰(zhàn)印跡 傳承復(fù)興力量 全國地市媒體紀(jì)念抗
- 9咸寧職工互助保障撐起健康“保護傘” 最大單筆
- 10全國智慧法院創(chuàng)新案例揭曉 咸寧市一個案例上榜
娛樂新聞
-
人藝“經(jīng)典保留劇目恢復(fù)計劃”開篇之作 《風(fēng)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