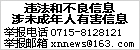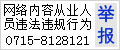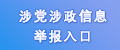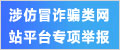深情
我的家鄉在鄂南山區,各類野獸活動在深山密林之中,緊挨山邊的莊稼常跟著遭殃。各村成立的護農小組中,父親年輕時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銃手。
后來,山下的莊稼人開始一茬茬往城里卷,山上的野獸下山無食可覓,便很少再來作孽,以往熱鬧的圍獵隨之沉寂了,而父親此時也老了。
平日里,父親侍弄完屋檐外廊墻角的幾丘菜地,余下來的時間,還是喜歡一個人拿著那支老式的單管獵槍上山轉悠。只是年歲大后,從前扛在肩上的獵槍,如今拄在腳邊,成了一支看起來很滑稽的拐棍。而他總是說:“轉轉吧,習慣了咱湖村的山,轉轉也好。”特別是落雪的冬季,父親每隔兩日,必定在清早進山一趟。
就是這樣一個冬季,父親遇上了那個人。
那個人,父親時常在我們湖村周邊碰到。籠著霧泊著小筏的湖邊,裊裊升騰著炊煙的早晨,更多的時候,父親會在密匝匝被夕陽涂得金燦燦的林子里遇到他。那些橡樹,槲樹,青杉,松柏什么的,平日里莊稼人司空見慣的樹們,在那個人眼里像鍍過金的寶貝。有時他弓著腰,有時會曲膝半蹲著地,伴隨著那個人手中的玩意兒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燈光閃過,有時還會嘩啦啦一下跪在地下,樣子莊嚴肅穆,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慶禮。再看那個人時,父親就常常忍不住多瞅幾眼,更多時候會瞅他背上封得嚴嚴實實的洋玩意兒。
那年冬季的雪很大,母親的阻止沒能如愿,反而加速了父親進山的頻率——隔日一趟變成了一日一趟。
那天一大早父親又拄著他那桿老獵槍,鬼鬼祟祟地瞞著母親從菜窖里拎出一條棉布小袋,踏著積雪穿過村口,走上了村后被落雪鑲白過的南攏凹。那被大雪厚厚覆蓋的山路上,一行腳印直向鑲白的樹林子,一股夾雪的寒風在父親錯愕的神情里吹動樹條子上綴滿的冰掛。
順著那行腳印,父親很意外地在南攏凹岔路上碰到了那個人。他立在路邊,似在等著什么,背裹里封得嚴嚴實實的洋玩意兒覆上了一層薄雪。迎著父親的目光,他笑笑算是打了招呼,然后跟在父親身后,也上了山。
父親拄著獵槍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來,他緊了緊手中的棉布袋子,看著同時停下來的那個人,折返身向另一座山頭走去。那個人在原地僅停了一下,也折轉身子跟向父親身后。
父親再次停下來,看著那個人,拄著的獵槍在雪地上不滿地跺了跺,一動不動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個人。那個人在父親的目視下,后退了幾步,復又走上前,父親的獵槍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,一動不動地望著他。那個人停在原地半響,才背著包一步一回地繞向另一個山頭。父親站在雪地中,直瞭見那個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個小黑點時,才轉身向南攏凹的深山走去。
父親在晌午時拄著獵槍空著手走進家門,棉布袋中裝著幾粒不知名的樹木堅果,他邊拍打著肩上的殘雪,邊絮絮叨叨地嘮著那個人的不是,嘮那個人擾了他的好事。母親見此很不滿地在一旁接口:“就是沒人驚擾你,你平素不也照樣是空手回家的。”而父親聽罷,嘻嘻哈哈地笑了。對此,我們再一次把父親所有的舉動歸咎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。
這件事不久,我應同事約,陪他參加一個攝影大賽的頒獎會。
在獲獎作品展廳中的一角,一幅叫《深情》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:雪地里半蹲半跪著一位老人,老人的模樣慈眉善眼,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,是一只灰色的野兔,看到老人,灰兔眼神像極了委屈的孩子,掙扎著向老人身邊挪近,一旁的雪地上,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,幾只鮮紅的蘿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。遠處一棵楓樹,被積雪壓彎的樹椏下,隱隱有支陳舊的單管獵槍在雪風中飄。 (徐建英)
編輯:Administrator
① 凡本網注明"來源:咸寧網"的所有作品,版權均屬于咸寧網,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并注明"來源:咸寧網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。
② 凡本網注明"來源:xxx(非咸寧網)"的作品,均轉載自其它媒體,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
③ 如因作品內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30日內進行。

娛樂新聞
-
人藝“經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”開篇之作 《風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