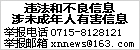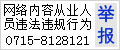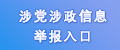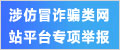寄語杏林
蜷曲在城中鬧市區半個多世紀的縣醫院,在東北郭的依山傍水處舒展了身肢,時值二0一二年歲尾。雅致巍峨的樓群,公園般開放式的場院,莊嚴恢宏的氣派,煞是叫縣人歡欣。
年后一個細雨綿綿的春日,我和一幫文友受邀來到這里。儒雅的張祖德君娓娓介紹,手指在鍵盤上靈巧跳動,圖文并茂的把整個醫院的前世今生、滄桑巨變、部位功能設置、十八般兵器,解析得條縷分明,我們為家鄉的人文進步感奮。講到治院理念,張君角色倒置,設身處地,將心比心,談對人才的渴求,對高境界醫德醫風的膜拜……話語古道熱腸,至情至性,我不由再次注目這位作為院長、專家的赤壁人。
能寫點什么呢?實話說,這是個少有詩情美感的所在,健康人甚至為之忌諱。來往寄住的是悲苦的人群,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藥味,仁慈的救治也充滿了刀光剪影和血腥,幸福的降生伴隨著撕心裂肺的哀聲,稚童懼怕醫生護士,甚于荷槍的警察。
真該寫點什么!為這座護佑桑梓百姓健康和生命的殿堂,更為在這里日夜忙碌的白衣天使。我的兒女在這里呱呱墜地,年邁的雙親經常來此祛病除疾,春秋數十載,這里挽留了多少親情和愛戀,成全了多少拳拳孝心,枯萎終成萌發,絕望化作歡欣。于病疾纏身的大眾,這里遠重于信徒心中的佛堂道場,諾亞方舟,沒有虛幻的精神麻醉,卻是實在的人間救贖。
十二歲那年在鄉間,正是伏月,我得了一場怪病。每天高燒灼人,頭痛欲裂,天地在眼前翻轉,旋即寒冷徹骨,渾身抽搐,數重棉絮也壓不出一絲暖意。鄉村的湯藥無濟于病,一連旬日,周而復始。少年的我對世界充滿了恐懼和絕望,連天亮前的雞啼也聞之驚心。
淚眼不干的外婆顛著小腳去了遠處的公社醫院,那時候的鄉村都有來自城里科班出身的醫生。中午時分,外婆身后跟來了滿頭大汗的白衣人,他放下藥箱,拽過竹椅坐在床頭,操著異地口音細細間診。起身時,他取了小包黃黃的藥片,輕摩著我的頭頂,話語溫軟:“孩子,是瘧疾,吃了藥不礙事,記著,以后有病及時去醫院。”說罷,推卻茶飯,在烈日下匆匆離去。
第二天,我病癥全無,頓覺日朗風清,為此,我終生記住了他的名字和那張棱角分明、清瘦的臉;為此,日后我執意找了個做醫生的妻子。
醫者,仁者仁術也,古來社會以良相良醫并論。軒轅帝醫濟天下,神農氏遍嘗百草,醫道是中華古文明的源頭之一。在官階森嚴的封建社會,人們尊稱醫生為大夫,連江湖游醫也喚作郎中。我們這輩人部曾熟讀過當代開國領袖寫的一篇祭文,是紀念一位殉職的異國醫生。為著他救死扶傷舍家國的情懷;對醫術精益求精的孜孜追求;滿腔熱忱忘我的工作態度,文中稱他是一個高尚、純粹、有道德、脫離了低級趣味、有益于人民的人,把他的精神總結為“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。”多么絕對的贊譽,偉人不惜與之畢生罵行的辨證法相悸。
記得那年初上廬山,我竟傻傻的詢找一個叫董奉的醫生的蹤跡,渴望見到那片蔚然壯觀的杏林。普濟蒼生,分文不取,唯愿人間杏白桃紅,時光逝去一千八百年,可敬的賢者,您在哪里!
健康乃人生之根本,祛病除疾是醫院的核心價值,驅除病魔要靠內行的良才圣手,高超的醫技源自敬業、勤奮、鉆研、培訓,庸官誤國,庸醫誤命,拒絕平庸應是醫者的天性。在愁云籠罩的床房,一臉真誠微笑就似一縷拂面的春風,爽貼的人文關懷也是一劑沁人心脾的良藥。
眼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尚不健全,大多數人家也不寬裕,當患者把痛苦的腳步和求助的眼神投向醫院時,他們從懷里抖抖索索掏出的,也許是嬰兒的奶粉、子女的學費,乃至闔家老小的全部生計。我知道,醫院并非慈善機構,醫生也是食人間煙火的凡人。醫療領域的
圣潔,在于她能于光怪陸離的商品經濟中,自覺擯棄市場化的操作,閃耀著人性的光輝。
人們憎惡人間病魔,也痛恨社會腐敗,我不敢相信,在這萬古風浩蕩的空間,有終日殺菌消毒的環境,也會讓紅包、回扣、輕慢、冷漠的“病毒”橫行。果真如此,人們真該悲哀,這個社會的腐朽將無可救藥。
我聽過一個叫李文霞醫師的事跡,他的名字已鐫入共和國的英模譜。人們笑談,此君其貌不揚,卻是邑內一尊實實在在的守護神,值得供奉;我看過一個叫劉慧敏護士寫的文字:戴燕尾帽的姑娘在病房的穿梭中紅顏漸褪,見慣了世間的大悲大痛,依舊保存著溫存、敏感、細膩的心靈。文中流露的那種憐惜患兒的母親情懷,讓我感概不已。
我仰望著高聳的醫院大樓,期盼并且相信,白衣天使們會為她注入崇高精湛和煦的醫德醫術醫風的靈魂。春陽暖暖,愛意融融,家鄉的土地上,也會出現那片蔚然壯觀的杏林。○甘振雄
編輯:Administrator
① 凡本網注明"來源:咸寧網"的所有作品,版權均屬于咸寧網,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、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并注明"來源:咸寧網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。
② 凡本網注明"來源:xxx(非咸寧網)"的作品,均轉載自其它媒體,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。
③ 如因作品內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,請在30日內進行。

娛樂新聞
-
人藝“經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”開篇之作 《風雪夜歸人》4月25...
 2025-03-27
2025-03-27
-
摘下神探濾鏡 《黃雀》講述充滿“鍋氣”的人物和故事
 2025-03-27
2025-03-27